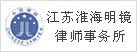作者:杜中奎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不知不觉父亲杜玉先已离我们而去20年了。今年的清明节,作为子女,我们进行了一场小型祭奠活动。追思中,最让我们子女怀念的是老父亲所从事的祖传手艺——染匠。虽然这种手艺,随着时代的发展,科技的进步,已经被历史所淘汰,但在五十、六十年代它是养活我们一家十几口人的经济支柱,也是我们姊妹衣食无忧、快乐成长的最大保障。

起 步
染坊店,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,了解的不多,但要是看过侯勇主演的《大染坊》电视连续剧或者去过乌镇旅游的人来说,应该了解一二。
五、六十年代在农村生活过的老年人,对手工印染有所了解,因为那时候有色布很少。人们穿的衣服,盖的被子,多数都是手工印染的。
我老家在邳州北部,与山东的兰陵、横山搭界。据说,从我太爷爷开始,就已经在老家从事手工印染手艺了,到我父亲,已传承了三、四辈之多。印染的生意多在邳州岔河、邢楼、四户三镇农村,远的辐射到山东横山、兰陵的部分乡村。由于印染质量高,服务态度好,价格低廉,在十里八乡,我们杜家染坊店也算远近闻名。杜家染坊店既是对我家生意的称呼,更多是含有对我家做生意有信誉的赞许。
二、三十年代,由于兵荒马乱,民不聊生,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,哪还有钱染布做衣服。祖辈们只好关闭染坊店,和大家一起逃荒要饭,艰难度日。
全国解放后,老百姓过上了安稳的日子,日子都慢慢好起来。我爷爷又把印染手艺拾掇起来,杜家染坊店重新开业。
印染,是纯手工体力活。店里接来乡邻手工织的白粗布,首先要浆洗,然后在大染缸里染色,染制完成后,要清洗浮色,再晒干。如果是印染花布,在染色前,先要用豆面和石灰粉调制成糊状,通过花板在白布上印出需要染制出的花纹(豆面和石灰调和后,在布上附着力强,不浸透颜色)再进行染色,染完后再把它刮掉,最后就成为印花布。
我的大伯、二伯和父亲,从十几岁就跟着爷爷打下手,学习印染的每道工序,也算给爷爷做帮手。每种染色缸中,需要加入多少颜料,能染多少布匹,侵染多长时间,爷爷都会交代。久而久之,他们自然掌握了手艺技巧。
五十年代,随着百姓生活不断好转,每到秋冬换季,人们都会买些无色布料(当时有色布价格昂贵,量也少,一般老百姓买不起),染成毛蓝、藏蓝或花布,更换衣裳、被面和包袱皮子。然而,正当染业逐步有起色时,爷爷突然病逝。二伯和父亲正值年轻力壮,为了我们一大家人的生计,他们接过了爷爷的手艺,正式成为杜家染坊店的新一代掌门人。

鼎 盛
在农村,印染业生意最兴隆时期,当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,大约有二三十年的光景。
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推进,人民安居乐业,农村生活也逐步好起来。吃饭、穿衣是每家的必须,因此,印染生意愈来愈火红。
五十年代末,我的四爷爷(姊妹排行老四)当兵转业后,自立门户开染店,赶四户集,承揽四户周边乡村百姓的印染生意。大伯转业后,由于身体原因,不能干重活,只能在店里帮忙。所以,杜家染坊店主要是由二伯和我父亲打理,父亲为主,二伯为辅。赶集上店、打货揽生意多数都是父亲。我家主要是赶大固集,承揽邢楼、岔河各村的印染生意。由于生意涉及的乡村区域大,印染的业务量也相当大,每逢秋天衣服换季时节,仅靠大伯、二伯和父亲他们是忙不过来的,我们家里大人小孩齐上阵,男女老少都帮忙。
父辈自从干印染后,我们从来看不到他手上皮肤的颜色,因为他每天都要用手在染缸里翻倒布匹,手常年是蓝黑色。

杜家染坊店的生意好,在邳北享有声誉,主要是我们家印染的颜色正,不掉色。早年多用的是山东南部兰陵、临沂农民种的染料植物制作而成的“蓝靛泥”,不含化学成分,但色调单一。后来随着我国工业发展,生产出硫化蓝、硫化青染料,染色逐步多了起来。我父亲经常到徐州及萧县的黄口镇购置染料。
徐州,作为苏北的第一大城市,但卖手工染料的店不多。黄口,作为皖北第一大镇,市场当时较为繁华,销售农村需求的物资品多,也能买到需要的染料。
儿时,我的父亲经常讲黄口多么好、多么繁华,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记忆,也十分向往到那里看看。
二十年后,我参加工作,曾多次因工作需要到黄口镇。漫步于黄口镇街头,总想找回我父亲口中的黄口。然而,映入眼帘的,与我想像中的差距很大。这也许是时代变迁,各村镇发展起来了,黄口镇市场自然受到影响吧了。
我家印染花布所需的花板,徐州地区很少有售。父亲多是到苏州的官前街去购买。当时,观前街有一家姓俞的老板(老板叫俞仁发) ,专做印染花布的花板。花板是用牛皮纸复桐油粘合而成,大概需要敷上五、六层,每面都要敷上桐油,使之紧密粘合,晾干后,再在板面上镂出花纹图案,以便印制。俞家的花板,有弹性,不易折,且图案多,深受印染业的喜爱。由于长期合作,俩家建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,有时父亲无暇去苏州购买,他们都会帮着邮寄过来。

父亲做生意,不仅讲诚信,而且讲仁义。质量上让百姓信得过,价格上比同行落低些,遇到结账时,真是差个毛儿八角,从不计较。有时用户(较为熟悉的),一时手头紧张,记个账也可以拿走。所以也赢得了百姓的信任。
小时候,记得父亲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:大概是1963年前后,苏北、鲁南地区,由于遭受天灾,加之其它各种因素,百姓家家闹饥荒。有一天,台儿庄泥沟村的一刘姓人家,家中老人得了病,刘家把仅有的几斤黄豆背到我们村赶集,想卖掉黄豆换点钱,给老人看病。下午三四点钟,眼看集市已经罢了,黄豆还是没卖掉(当时的环境下,有钱买粮食的人家不多)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他无奈地走进了杜家染坊店,向父亲道清原委,请求父亲能买下黄豆,父亲了解情况后说,这几斤黄豆是你家保命粮,带回去给家人度饥荒吧。至于给家人看病,我可以借点钱给你,暂渡难关,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。
后来,刘姓人家境遇好了起来,他们每年都会来我们家,给我们家带些自家种的土产,两家成了亲戚走动。厚道经营,一传十,十传百,有许多相距二三十里的村民,会专门到我们村赶集,来我们杜家染坊店。
六七十年代是杜家染坊店最鼎盛时期。我们家面临街道,为了晾晒染好的布匹,门前立着高六七米高的晾布杆,每天都有许多染好的布需要晾晒,各色布在空中随风飘扬,我家门前就像插着五色旗,引起无数路人停步瞩目,也是当年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那时,杜家染坊店每月能有多少盈利?由于当时我们都小,没有亲自参与过账务,父亲也没有讲过,所以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每月税务所到杜家染坊店收税钱,据听说,多在二三十块钱。记得一年秋季,最高的月份税收过八九十块的。
这个数目,在现在算不了什么,但要知道,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,一个鸡蛋也就二分钱,猪肉也就七毛钱左右。农村一个棒劳动力,干一天农活的价值也就一毛多钱。 由于我们家开染店,生活相比邻居们要好一些,兄弟姐妹们在童年时没受多少苦。
记得1965年,我上小学的时候,父亲从徐州打货回来,为我买了双塑料凉鞋,我高兴地跑到小学校(学校距我们家三四十米)来回跑,生怕人家看不到似得,好多邻家小伙伴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。
也正是父辈的手艺,支撑我们弟兄几个学有所成,相继考学,离开家乡。

衰 落
印染业的衰落,是社会进步的象征,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。
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结束,国家的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,经济在发展,科技在进步,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在提高,百姓的吃饭、穿衣需求档次也有了很大的提升。
七十年代初,国家大力推行集体经济。个体手工业者都不允许私自经营,全部收归集体,被称之为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。当时的人民公社、生产大队,各自根据区域特点,把手工业者集中起来,成立小型的练油厂、酿酒厂等。
我们村也成立了由我的四爷爷、二伯、父亲爷仨组成的大队染坊店。所有印染用具都是我们家提供,大队提供场所,派进一个负责人和一名会计,核算收益归集体。大家在集体染坊店干活,按日记工分计算劳动报酬。
应该说,大队的集体印染店,开始几年,效益还是可观的。虽然,有色布已有生产,但农民生活还相对贫穷,大多家庭还不舍得买有色布做衣服,还是买些白布,染一染,物美价廉。
但到了八十年代,随着科技的发展,各种颜色的化纤布料面世,市面上出现了涤确凉、涤纶、涤卡各色新式布料。且随着百姓生活的好转,手头宽裕了,自然穿手工染制衣服的就少了起来,印染店的生意便慢慢的萎缩了,经营难以为继。
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,1978年我被某大学录取,要去外地上学时,想做一身新衣服,父亲还要坚持为我做自家染制的棉布料,我却不乐意,我给父亲说,你看看咱们村的青年人都不太穿染的布了,我再穿染的布,城里人不笑话我吗?最后还是母亲替我做通了父亲的工作,为我做了一件涤卡衣服。
后来,我才明白,父亲不是不想让我做涤卡衣服,主要还是思想守旧,认为传统的纯棉布结实、耐穿。再就是因为印染没有了生意,家里断了经济来源,手头没有宽裕的钱添置新潮色布料子......
不久,大队的集体染坊倒闭后,父亲就只能靠种地维持家中生活,幸好的是,不几年我家弟兄几个相继考学,也都有了自己的事业,这也是对他一生最大的安慰。
1992年,邳州撤县建市,市里想用蓝印花布制作一批手提袋、布包、方巾等具有地方乡土气息的工艺品,作为建市纪念。为此,在市政府工作的表哥,还到家里找我父亲联系,想看看能否赶制部分蓝印花布,由于父亲年事已高,体力不支,加之染制物具不全,未能成全此美事。
由于长年的生意所累,晚年的父亲,身体不甚好,体弱多病。那时,我们兄弟几个才刚刚参加工作,没有多少钱照顾家里。因而,父亲把家里存的染布花板和布牌子,以六十块钱的价格,卖给了我们村的一个王姓的民俗爱好者。

在父亲离世的前几年,还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,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,就是没把祖传的手艺传给我们,印染手艺在他手中失传了。我劝慰父亲说:“印染手艺已经被时代淘汰了,新的印染技术已取代了传统印染方式,学了也用处不大。再说,我们兄弟都有自己的工作,总不能回家传承您的手艺吧”?
杜家染坊店相传几代人,这不争的历史,谁来续写?
待等我们退休闲暇下来了,再做些业余研究,传承祖业吧。
父亲的一生是敬业的一生,他把祖传的手艺做到了鼎盛;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,无论生意多累、生活多苦。他都无怨无悔;父亲的一生是仁爱的一生,他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做事;父亲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,无论生活多么困难,他都坚持让我们上学,用知识改变命运。
前一段时间,我在老家弟弟家里,拍了几件当年父亲开印染店时所用的工具,展示出来。也算是对父亲的追思与纪念吧!



声明:该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本号为信息存储平台
信息来源:时代淮海








 苏公网安备 32031102000168号
苏公网安备 32031102000168号